
背景故事之
望 斷 關 河 念 顧 公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新 亞 山 頭 北 望 八 仙 嶺)
引言、「向中國出發」之前……
大家看過多期的背景故事,就應該知道,「背景」云云,都是我多年來旅行時拍下的照片,「故事」云云,都是我的一些旅行感想與因應著我的信仰關懷進一步的借題發揮。按此推論,今期以「香港中文大學」為題,難道我要寫一篇「中大遊記」麼?
非也!非也!
今期背景故事裡頭的照片,大多是我二十年前在中大讀書時拍下的,應該不算旅行照片吧!中大校園雖然是出名風光明媚,但我那幾年(1986-1990)的「中大日子」,怎麼也不算「旅行歲月」吧!不過,數典不可以忘祖,大家卻不可不知道,沒有我二十年前的「中大日子」,主觀上講也好、客觀上講他好,很可能就沒有我隨後二十年的「旅行歲月」呀,後果「非同小可」。
先從主觀上講,觸發我隨後二十年的「旅行歲月」,一年起碼數次「向中國出發」,遍遊大江南北、走訪名人故地的因緣,就發生在我的「中大日子」裡。
在中大中文系學習的四年裡,我「結交」了三個了不起的「朋友」--唸《楚辭》時結交了屈原,讀《杜詩》時結交了杜甫,讀《魯迅專題》自然就結交了魯迅了。這些人物,我中學年代就認識,也打過「招呼」,但遠遠算不上「深交」。結為深交,是在中大的這幾年裡。事實上,中大校園的環境確更能引發「讀書人」與情緻,春晨秋暮,或在山頭湖畔吟唸他們的詩詞佳句,或在圖書裡館博覽他們的鉅著文章,幾年間,就結成了莫逆之交了。那個時候,就常常意想,他日有緣,自當登門造訪。果然,我日後二十年的所謂旅行,訪尋屈原、杜甫、魯迅三位「朋友」的縱跡,就佔了我的行程的大半了。


山下荷花池與池中睡蓮,下山小路灑滿石階的油桐花,就算不是詩人,見這般景緻也會油然有幾分詩興
好了,有了主觀願望,但還要有客觀條件,因為旅行,畢意是要花費相當的金錢和時間的。
再說這幾年「中大日子」,竟然讓肯定「不善營生」的我也能馬馬虎虎弄到個「學位」,繼而又馬馬虎虎弄到個「教席」。那個時候,金融海嘯聞所未聞,「殺校」更是匪夷所思,當教師自然也要受氣(受學生氣),但斷沒有今天那樣的繁重工作與沉重壓力,最妙的是收入不薄,假期又多,這樣,就為我其後多年的「旅行歲月」奠下了必不可少的「物質基礎」了。
大家看到嗎?若我說沒有這四年的「中大日子」,就沒有我隨後二十年的「旅行歲月」,也沒有可資寫成「背景故事」的題材,甚至連「俄巴底」也沒有(至少不會有現在這個「版本」的俄巴底)……大概是沒有誇張的啊!
換句話說,在我既有意識又有能力地「向中國出發」之前,先「向中大出發」一定是我更早走過的一段路。然則,我又是如何走上這條「向中大出發」的路的呢?……
一、我的「中大之路」
這是二十年前我親自拍攝的中大校園正門--我是怎麼走進這門口的呢?
這是網上取來的現在的中大全景。與二十年前的最大的分別,是白色(建築)部分多了,綠色(草木)部分少了
今期背景圖片(左下小圖)所展示的,是我大約二十年前站於中大山頭(紅圈位置)往北望八仙嶺所見到的景緻
長話短說,我既喜歡中國文學,那個時候,要在這方面進修,實在沒有太多選擇,報讀中大中文系是很順理成章的,倒沒有甚麼好說。我更沒興趣講我如何勤奮力學學有所成的「見證」,因為成績比我好、學問比我高的人滿街都是,哪有甚麼「見證」?
在這期背景故事裡,我最想說的,是入讀中大,讓我結成日後與屈原、杜甫、魯迅的「隔世姻緣」,但導引我入讀中大的,卻原來又是另一段的「隔世姻緣」。
所謂文史哲不分家,喜好文學、歷史的我,自然也會涉獵一些簡單的哲學。
記得信主之初,因為同是基督徒的關係,也因為是某種「校友」的關係,更因為我對中國哲學有點興趣的關係,就經常聽梁燕城的講座(有現場的,有錄音的)。梁君口中提得最多的,不是孔子、不是孟子,而是他的恩師唐君毅先生。我生得太晚,入讀中大的時候(1986年),唐君毅先生已經去世八年了。這裡,先簡單一敘唐君毅先生的生平。


唐君毅先生遺照 與謝廷光女士攝於婚前(1941年) 講學中的唐君毅(攝於50年代後期)
唐君毅(1909-1978),四川宜賓人。中國現代著名哲學家,與牟宗三、徐復觀等並為新儒家的代表學者。少年時期於四川家鄉完成中小學教育,17歲入北京大學聽課,聽過胡適、梁啟超、梁漱溟等學者講學,而受梁漱溟的思想啟發尤多。後轉到南京中央大學就讀哲學系,其時在該校任教的著名學者有方東美和熊十力等,於1932年畢業。
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不少新進知識分子主張「打倒孔家店」,推翻封建傳統,胡適更倡議「全盤西化」,共產主義又乘時崛興於中國,對中國傳統學術文化,造成巨大衝擊。其時,部份知識分子開始重新思索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唐君毅就是其中之一。
唐君毅一生以闡釋儒家學說的合理性及價值為己任,特別是立根於現在觀點,指出儒家思想對現代中國的意義,尤其著重中國文化中的人文主義以及道德自我的自立。
唐君毅十分重視青年在中國文化方面的培育,抗戰期間,他歷任四川、華西、中央等大學教授,後任無錫江南大學教務長。
1949年,康君毅南下香港,與錢穆等學者創辦新亞書院(後與崇基書院、聯合書院合併為香港中文大學),以繼承宋代書院講學的傳統,弘揚中國學術文化為辦學宗旨。他也先後擔任新亞書院哲社系教授、系主任及教務長等職。1963年,香港中文大學成立,新亞書院成為中文大學成員學院,唐君毅獲聘為哲學系系主任、講座教授及文學院院長等職。
1974年自中文大學退休後,繼續出任為新亞研究所所長。1978年因患肺癌而逝世,享年六十九歲。
資料節取自:http://sjs.hkcampus.net/~sjs-chin/article101.htm
老實說,對唐君毅先生的學問我知之甚少,他的書,我認真讀過的也只有比較「通俗」的幾本,譬如《青年與學問》、《說中華民族的花果飄零》和《人生之體驗》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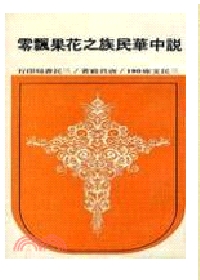
至於「新儒家思想」,我更沒有認真研究過。畢竟我已經信主,從「信仰內容」上講,自然與唐先生的有一定的距離。不過,唐君毅先生卻有一種很偉大的「信仰人格」,非常非常的感動我,甚至呼喚我「慕名」報讀中大,雖然他那時已經去世八年……
簡單說,促使我入讀中大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想當教師的理想(詳見《我的見證》);二是對中國文學的興趣(已見上述);三是對唐君毅先生的信仰人格的崇敬,俗氣點說,就是希望在中大沾一沾他的「靈氣」(請看下文)。
二、望斷關河念顧公
我與唐先生的這段「隔世姻緣」,容讓我又「大而化之」,用我以下這首「詩」交代吧。
一九八八年,是我入讀中大的第三年,也是唐君毅先生逝世十周年。這年,自然各方舉辦了一些紀念活動,在中大校園裡也有若干紀念活動。但在我的印象中並不熱烈。事實上,自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香港經濟逐步起飛,大學生大多「向錢看」了,甚麼政治關懷、文化理想都紛紛得靠邊站。唐先生的哲理思想,就連在中大裡面,也不見得有許多人問津。
那時,記得是要交功課,要作一首「近體詩」,適逢唐君毅先生逝世十周年,有感於心,便「一舉兩得」,寫成了這首《唐君毅先生逝世十周年有感》:
這首「詩」(姑且算是)詩意當然寥寥、詩景更是堆砌,全不足觀,但當中的詩情卻是真的,請忍耐著聽我道來:



秋水潺湲倦晚風,秋山縈繞勢如弓
中大山明水秀,視野遼闊,東臨吐露港,北望八仙嶺。立於中大新亞書院的山頭,往下望是緩緩流動的秋水,晚風輕拂,更是意興倦人;遠望則見群山環抱,氣勢如同重重的彎弓。以上是「實景」,寫的是眼前廣遠開闊的景象。【見上左起第一圖】
空臨落日舖千嶺,別有愁雲蕩五中
這兩句寫的是「半虛半實之景」。眼前縱然有「落日」餘輝,但並不是想寫「落日」,而是想寫「空臨」(百無聊賴地呆望)中的寂寞之情。「愁雲」自然更是「無中生有」的,不是要寫天上真正的「雲」,而是要寫滿心「愁」意在「五中」(指內心)翻盪的悽然之感。
巨塔含情思古靜,蒼松抱憾落花紅
這兩句是由遠及近,又由景入情。中大有兩座大型水塔,是中大山頭的著名地標。【見上左起第二圖】中大山頭也遍植松樹和各色花卉,三、四月間更是遍山的「杜鵑紅」。【見上左起第三、四圖】然而「巨塔」又怎能「思古」?「蒼松」又豈會「抱憾」?……
艱難未作東林客,望斷關河念顧公
原來,「思古」的是我,「抱憾」的也是我。
這裡先解一解句中的典故。詩中的「東林」二字指的是無錫的「東林書院」。明朝末年,這裡聚集了好些憂懷國是的學者文人,在此議論時政、抨擊時弊。後因得罪當權的宦官魏忠賢,書院竟遭封拆,書院中人(統稱「東林黨人」)亦慘遭迫害。至於「顧公」二字,則是我對當時東林書院的主要領袖人物「顧憲成」的尊稱。大家應該聽過的「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就是出自顧憲成的手筆。
東林書院的遺蹟
記得我中學讀中國歷史的時候,最令我悲憤不平的有三件事:第一件是岳飛慘遭誣害;第二件是鴉片戰爭中我國的喪權辱國與英國的卑鄙無恥;第三件就是明末宦官的橫行禍國,並因而特別同情東林黨人,於是乎「東林」、「顧公」就成了我心目中的某種「學者式」的英雄典範。當然,放在這首《唐君毅先生逝世十周年有感》中,「東林」和「顧公」自然別有所喻,就是借以寄寓我對唐君毅先生的人格、學問、努力和理想的崇敬與懷念。
然而,我生得太晚,無緣一睹唐君毅先生的人格與風采。「艱難」地考進了中文大學,卻無緣一作「東林」的座上「客」;只好佇立於中大山頭極目遠望(「望斷關河」),遙念這位緣慳一面的「顧公」--唐君毅先生。於是乎「思古」(想象當年),於是乎「抱憾」(傷心今日)……宛似秋日的「蒼松」深恨無緣得見春日的「落花」一樣。
我前面說過,我讀過唐君毅先生的作品甚少,卻是「感動」何來呢?並且至於要「慕名」報讀中文大學以致落得後來的「思古」而「抱撼」的下場呢?答案「大而化之」,就可以在以下兩篇短短的(按唐先生的作品規格而言是極短了)文章之中找到……
三、看哪!這才是信仰!
實話直說,我信主將近三十年了,但在現實的所謂基督教「圈子」裡頭,能夠真正感動以至震撼我的「信仰人格」,抱歉,連一個也沒有遇上。卻是在教會圈子外,我竟然找到了一個,就是唐君毅先生,他給我「看哪!這才是信仰」的極大震撼,說來真不知是悲哀,還是緣分。算了,我且又「大而化之」,請大家耐心細讀以下兩篇唐先生的文章,再參看我附於其下的小小「讀後感」,就可知其大概了。
記得,大家讀的時候,自然要適當地過濾和取捨,畢竟,唐先生不是基督徒啊,不可能講出「正統」的基督教。另外,若怕在屏幕上看長篇文章,可找《青年與學問》一書來看,以下兩文是該書的附錄。
1、《告新亞書院第六屆畢業同學書》
(一)
本屆畢業同學﹐都是在我們學校未與雅禮協會合作以前到學校的。再下一屆的畢業同學﹐便不是了。我們學校之與雅禮協會合作﹐當然是本校校史上之一最重要的階段。沒有雅禮協會的合作﹐使我們學校﹐能有新的校舍﹐得增加許多好的先生與同學﹐我們的學校不會有今天的進步﹐亦不會使社會上都逐漸知道我們的學校。對於雅禮協會的合作﹐我們當然是應該感謝的。但是我卻總是不能忘懷在與雅禮協會合作以前的我們之學校之一段歷史﹐而對那時到學校的同學﹐另有一種感情。而到你們這一屆的同學畢業後﹐則原來的同學都完全離校了。這使我覺得有些話﹐不能不藉此機會說一說。
我之所以懷念我們學校在未與雅禮協會合作以前的一段歷史﹐不是說那時的新亞之精神比現在好﹐亦不是說那時的先生與同學們更能堅苦奮鬥﹐更像一家庭等。我所想的﹐只是那時我們之學校甚麼憑藉都莫有。如校歌中所謂「手空空﹐無一物」。我個人那時的心境﹐亦總常想到我們在香港辦學﹐是莫有根的。我們只是流浪在此。我們常講的中國文化精神﹐人生理想﹐教育理想﹐亦只如是虛懸在口中紙上﹐而隨風飄蕩的。但是正因為我常有此流浪的無根之感﹐所以我個人之心境﹐在當時反是更能向上的。正因我常覺一切精神理想的虛懸在口中紙上﹐而隨風飄蕩﹐所以更想在內心去執定它。我由我自己的體驗﹐使我常想到許多流亡的同學﹐你們在香港更是一切都無憑藉﹐應更有一向上的精神理想﹐亦當更能執定它。我不知道畢竟你們這些流亡的同學﹐是否真能從流亡中真體驗到一些甚麼。但是以後我們之學校﹐卻斷然是流亡的同學一天一天更少或根本莫有了。而我們之學校﹐有了校舍﹐逐漸為世所知﹐在香港社會立住腳。我們之流浪無根之感﹐亦自然一天一天的會減少了。這畢竟是我們學校師生之幸呢或不幸呢?

這就是新亞書院草創時期位於九龍桂林街的「校舍」及現在的「遺址」,非常簡陋
但是我又不能說我們學校不當有校舍﹐不當逐漸為世所知﹐不當求在香港社會立住腳跟。一切存在的東西都要維持他自己的存在﹐並發展他自己的存在。如自己力量不足時﹐即希望其他存在的東西來幫助維持他自己的存在。學校之望有校舍﹐亦如個人之望有家宅。學校之望逐漸為人所知﹐在所在社會立住腳跟﹐亦如個人之在世之希望有所表現於社會而為人所知﹐而成就其事業。流浪飄蕩的生活﹐總要求有一安定休息之處。人只在內心有一向上的精神理想還不夠﹐人必需在現實世間有一開步走的立腳點並逐步實現其理想﹐此立腳點不能永是流浪飄蕩的。
由此我們可以了解一切個人的人生與人生之共同的事業﹐同有一內在的根本矛盾或危機。人必須在現實上之憑藉愈少而感飄蕩無根時﹐然後精神上之理想才愈能向上提起。但提起的理想又還須落在現實上生根。然而我們只注目在理想之在現實上生根時﹐理想之自身即可暫不向上生發﹐而現實的泥土﹐亦即同時可窒息理想之種子的生機。這是一切個人的人生與人生之共同的事業﹐同有一內在的根本矛盾與危機。這點意思﹐我希望大家能有一真切的會悟﹐然後再看我們有無解決此矛盾與危機之道路。關於此一點﹐我想關連到各位同學畢業後之切身的出路問題﹐從淺處一說﹐然後再回頭來說我們的學校。
(二)
我們學校之畢業同學﹐以前幾屆都很少。從此屆起﹐則畢業同學越來越多了。究竟畢業以後﹐同學到那裡去呢?這些問題﹐不僅同學們自己關心﹐學校的師長們﹐亦一樣關心。以學校的師長之本心來說﹐真正的師長之望其畢業同學之各得其所﹐前程遠大﹐實際上與父兄之望其子弟之各得其所﹐前程遠大﹐並無分別。但是在畢業同學少時﹐學校之師長或能看見其畢業同學﹐都一一分別就業。而在學校大了﹐畢業同學多了以後﹐則一批一批的同學之畢業﹐從學校方面看來﹐即如同送一批一批的子弟﹐到前途茫茫的世界﹐亦不知他們將歸宿何所。而畢業同學一離校以後﹐命運各人不同﹐或升或沉﹐或順或逆﹐五年十年之後﹐或相視如路人矣。從此處想﹐實有無盡之悲哀。但人生無不散之筵席﹐任何好的師長﹐至多只能盡他的教導之責。但是對於盡責後之結果﹐則全不知下文如何。而此悲哀﹐亦成古今中外從事教育者無法自拔的命運。而此時我所能說的話﹐最重要一點﹐即是諸同學離校後要了解一個真理:即人生所遭遇的命運﹐其價值要由自己去賦與。同學畢業之後所遭遇之命運或處境﹐可以千萬不同。但大別言之﹐總是非順即逆﹐不是比較得意﹐便是比較失意﹐不一定學問好德性好的就會遇順境而比較得意。人之處境之順逆﹐有一半是偶然的。但同時我亦要鄭重說明﹐實際上一切順逆之境﹐都同樣可是對我們好﹔亦同樣可是對我們壞的。此好壞之價值﹐全由我們自己作主宰去賦與。我們通常說逆境是壞﹐但所謂逆境者非他﹐即人在現實上少一些憑藉與依傍而已。但是我們可以說人之精神理想之提起﹐正是由於人在現實上之莫有甚麼憑藉與依傍而來。所謂順境者非他﹐即人所想望者﹐或理想中者之比較能在現實上生根或實現而已。但是上文所述之現實之泥土﹐即可窒息理想之種子的生機。在此處我們須要認定﹐在大多數的情形之下﹐世俗上的幸運﹐都是使人精神理想向外下墜的﹐而世俗上的不幸﹐都是鞭策人之精神理想向內上升的。這個道理﹐古今之聖哲有無數的﹐足資證明。但是現代人大都忘了。我想即以此話勉勵畢業後處比較逆境的同學。
我這個的意思﹐當然不是要同學們不去求職業﹐不去求比較順適的環境﹐進而謀求學問事業之成就。但是我再要說明﹐如果同學們將來能得一比較順適的環境的話﹐同時千萬不要忘了一切順適的環境﹐都同時是宴安酖毒。以所謂「順適」、「宴安」﹐是最廣義的說﹐同時是比較的說。譬如說畢業同學有的希望留在學校﹐有的想留學﹐而亦竟然留在學校了﹐留學了﹐在此處同學們如果覺到好像有一依傍有一憑藉﹐這亦是一細微的宴安﹐亦是一酖毒。依同理﹐如果我們覺到學校有了校舍﹐有了外面的援助﹐社會的稱讚﹐此學校如可以有所依傍憑藉而永遠存在﹐此中亦有一細微的宴安。此念亦是酖毒。我常想人生有一件事﹐是要永遠要自己去勉勵自己的。即人在獲得了甚麼時﹐要覺自己並無所得。人在覺自己是甚麼時﹐要覺自己並無所是。所以畢業同學們如果能留校留學﹐仍要想自己如仍在調景嶺時一般﹐並不覺留校是學校可依傍﹐並不覺留學可增加我之立身處世的憑藉。我們學校儘管有了校舍與外面之援助、社會的稱讚﹐但我們亦須常想到社會的稱讚隨時可改為毀謗﹐外面之援助隨時可斷絕﹐火亦可把我們校舍燒掉。一切人所得所有的東西﹐原都是可失可無的。一切人今天是如此﹐明天都可不是的。這些話不是只當作抽象的道理來理解﹐亦不是只當作一可能的想到來理解﹐這要真正設身處地來理解。人真正要作到要忘掉他自己之所得與所有﹐當然不容易完全作到。我自己亦不能作到。譬如許多同學要問我此次由日本到美國有甚麼感想?我的感想之一便是我未能忘掉我之所是。如我是一哲學教授。在接觸人的時間﹐實際上別人亦如此看我﹐更使我不易忘掉我之所是。但是我一人在旅館中或街上走時﹐因人地生疏﹐我都常想到我此時在他人前﹐不過一中國人。在此我亦即忘掉我所是之哲學教授﹐成了一純粹之中國人。而他人亦許不能分辨我是中國人或日本人﹐則我成了一純粹的人。此處我即有一解脫感。但是此解脫感﹐實並不需要由他人之如何看我反照過來﹔我知道我本來可以不是哲學教授﹐而只是一純粹的人。但是這種只是一純粹的人﹐此外甚麼都不是﹐甚麼都覺無所有之解脫感﹐我亦不能常有。但而我雖不能常有﹐我卻深信一個人要真成一個人﹐必須從忘掉自己之所是所有﹐而空無依傍上下工夫。而此亦是一切真正的智慧真正的理解、與真正的感情所自生之根源。這個道理似乎陳義太高﹐亦許諸位同學還不能適切的了解﹐但是我不能不以此期勉同學們。
(三)
由此再說到我們學校與雅禮協會等之援助的關係。據我所知﹐此間雅禮協會開會的結果﹐是要想募款﹐預備學校第二期校舍的建築。這我們自然應當感謝他們的盛意。而大家同學聽了﹐亦必然很高興。但是我要說﹐大家如只是高興﹐此中就又有一依傍憑藉他人的心理﹐這個心理並不是偉大的。而社會上的中國人因新亞有國際朋友的幫助而另眼相看﹐這個心理亦並不是偉大的。當然新亞書院需要人幫助。只要出自純粹教育的動機而來的幫助﹐無論是中國的外國的﹐新亞書院都是希望的。但是我們之此希望之背後﹐卻不能莫有一種複雜的感情。即我們須要想﹐何以我們不能憑自力來辦此一學校?何以香港的中國人不能以經濟力量支持此學校?這原因一直追上去﹐我們是不能莫有愧恥之感的﹔亦不能莫有哀痛之感的。而社會上的中國人必須待一學校在有國際朋友的幫助﹐才另眼相看﹐此亦猶如一些中國學生必須留學﹐一些中國學者必須經外國人品題敦請﹐然後才為國人所重。同樣是一種可悲可嘆的心理。這些心理﹐原因複雜﹐我不忍心說這全是中國人自卑自賤。然而至少其中有可悲可歎處。此處我們要真切的想﹐為甚麼一個國家不能自己樹立自己的學術文化標準與教育標準?又新亞書院與雅禮的合作﹐在雅禮方面的經費﹐本來是為辦教會學校用的﹐現在用來支持一非教會的學校。在雅禮方面﹐對其原初的理解是有所犧牲。然而此犧牲中卻更表現一真正無條件的幫助人之耶穌精神。現在我們自問﹐用甚麼東西去還報雅禮協會方面的同仁們所費的心血精力和金錢呢?當然﹐新亞書院亦使雅禮協會同仁們獲得一幫助中國人的機會。但是我們不能只以此來自慰﹐我們還須另有還報。我在此曾經這樣想﹐我想終有一天﹐中國亦會富強﹐這時亦會有新亞書院的畢業同學﹐用他們的心血精力與金錢﹐在美國幫助美國的基督教徒辦基督教的學校。但是我這樣想了﹐我們能對外國朋友說麼?我能有資格說麼?為其實使我有資格說?此中仍有可悲可嘆處。而我今對你們說﹐你們最初亦或將不免一笑。但是如果你們笑了﹐你們就有罪了。實際上照我的想法﹐如果我們不能發一願心﹐使中國成為頂天立地的國家﹐不僅能自立﹐而且能幫助世界﹐我們就不當接受國際朋友的幫助。新亞書院還是搬回桂林街的好。但是諸位同樣們能發此願心嗎?
我離香港數月﹐已經歷半個地球。但是﹐從見聞方面說﹐實在莫有甚麼多少增加。耳目所能及的﹐由書籍同樣能及。如果說此數月來真的得益﹐主要還是在自己的感情方面。我總覺到人類的人性是同一的﹐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如日本人歐美人﹐都有許多可敬可愛之處﹐值得我衷心佩服。在此處是莫有國家民族的界限的﹐但是在未達天下一家以前﹐一個人只有求真實地生活存在於其自己的國家民族與歷史文化之過去現在與未來之中﹐才真能安身立命。我儘可以佩服其他國的人﹐但是我卻從未有任何羡慕之情。我儘可承認他國的學術文化的價值﹐但我從未想任何國的文化可以照樣的移運到中國﹐亦從未想中國的學術的前途可以依傍他人。我隨處所印證的﹐都是一個真理。即我們要創造我們自己的學術前途與文化前途﹐我們無現成可享﹐亦不要想分享他人的現成。人在天地間所貴在自立﹐個人如此﹐國家民族亦然。能自立的人﹐亦需要人幫助﹐亦可以向人借貸。在物質上精神上我們同可借貸於人。但是我們必須在借貸時即決心要還。新亞書院受國際朋友的幫助是借貸﹔中國人之學習外國的學術文化亦是借貸。在此如果我們不能使中國富強﹐不能在中國學術文化之前途上有新的創造﹐以貢獻於世界﹐而亦有所幫助於人﹐則我們將永負一債務。我並時常想到﹐人生在根本上亦就不外是在求還人對其精神理想所負之債。人之精神理解愈高﹐則責任感愈重﹐而債務感亦愈深。人對照其精神理想來看自己之現實存在﹐不僅自己一切所有所是﹐都算不得甚麼﹐同於無所有無所是而且此自己之現實存在中﹐歸根到底﹐只有負面的債務﹐如永遠還不完。我想人亦或須常如此想﹐然後人才能真正的自強不息﹐然後任何現實的泥土﹐都不能窒息其精神理想的種子之生機。這些話的陳義﹐似乎又更高了。但是我請諸位同學試想我們在雖有校舍而無土地的香港居住﹐面對五千年文化存亡絕續之交﹐我們的生命中除了對於是中國古代之聖賢﹔我們之祖宗﹐千千萬萬的同胞及世界的朋友們之期望﹐未能相副之感與渾身是債之感以外﹐又還有甚麼? 此意望與諸同學共勉之。
你們諸位同學就要畢業了﹐但是我不特莫有甚麼話祝賀你們﹐亦莫有甚麼話安慰你們﹐我反而要說這許多話﹐來增加你們之沉重之感。但這亦是以後我再少有機會向你們說話的原故。
2、《我與宗教徒》
【按:首三段涉及一些較抽象和學術化的「宗教對話」問題,不易看,各位可直接由第四段讀起。】
魏澄平君是在道風山信義神學院研究神學的。最近寄交民主評論社二文﹐一文是為我人文精神之重建書中「人類精神的行程」一文﹐作一詳細的中西思想對比表。一文是基督教的觀空破執論。民主評論編者寄來要我加以審查。對於前一文﹐我感謝魏君之一番好意與所用的工夫﹐但認為不必佔據民訐的篇幅。後一文﹐我覺卻可刊登﹐而且願意附幾句話於後。
我之所以主刊登此文﹐是因此文表示一種宗教而兼學術的真誠。魏君是真切的感受到基督教的修養工夫中之某一問題。這問題﹐是基督教到中國後﹐中國基督教徒將基督教教理﹐與中國文化思想及已生根於中國文化之佛學思想對勘時﹐應碰到的問題。亦是我個人年來論到宗教時﹐常提到的問題。但是一般基督徒在此點上﹐常置諸不顧。這樣﹐基督教將永不能真正在中國文化中生根﹐因為它未接觸到中國文化思想的核心。而如真碰到此問題﹐則基督教亦必要開始中國化。在中國化以後的基督教﹐可能如佛教之中國化為中國之禪宗亦可能如中古之天主教之化為馬丁路德的新教。這是人類文化大流之匯合﹐必將有的一環。或必須經過的一歷程。魏君此文之本意﹐固不必是要使基督教中國化﹐但是他此文至少表示了他個人之一點真切感覺﹐而暗示出此中之有一基督教思想﹐與中國思想如何接頭的問題之存在。所以我主張加以發表。
魏君此文之內容﹐雖引了我許多意見。但我個人不必都贊成。一般基督教徒看了﹐亦可能說其走入異端。而其藉用佛家的觀空破執的名辭﹐認以為基督教思想作註釋﹐亦非佛教徒之所喜。但是亦正因如此﹐所以此文可使人感到上述之一問題之存在。這問題如何解決﹐不是簡單的話可說明的﹐我現在亦不擬在此討論。我想撇開理論﹐藉此抒發我對中國的真正佛教徒與基督教徒的一番敬愛之意。
我自己是生活在塵俗世間﹐而在自己生活上德性上﹐自知有無數缺點的人。我只想自勉於希慕儒家的賢者﹐而非任何的宗教徒。但對於虔誠的宗教徒﹐我實深心喜歡﹐這中間常使我生無限的人生感觸﹐人生體悟。我總與宗教徒﹐一直有緣。然而我亦總辜負他們對我的期望。我所最難忘的朋友之一﹐是中學時便同學的映佛法師。前輩先生中﹐則對於歐陽竟無先生﹐我亦始終仰服。但這都不在他們的知識與所講的道理﹐而在他們的為人。映佛法師的恬靜悲憫的情懷﹐歐陽先生之泰山喬嶽的氣象﹐都常在我感念中。歐陽先生本是我父親的先生﹐亦是熊十力的先生﹐應算我之太老師。對於他﹐我最不能忘的事﹐是在他七十歲的時候﹐他曾要我住支那內學院長為其弟子﹐並為我安排生活。我當時不肯。他於是大怒﹐忽然聲帶悲惻﹐說:「我七十年來﹐黃泉道上﹐獨來獨往﹐只是想多有幾個路上同行的人……。」我聽了黃泉道上﹐獨來獨往數字﹐便不覺深心感動俯身下拜。歐陽先生亦下拜。這是佛家的平等之禮﹐並非我皈依佛之表示。我當夜仍即離開了支那內學院﹐上船回家。這時歐陽先生的一學生﹐送我上船。時霧籠江畔﹐月光如水。這學生倚船欄向我說﹐今天是歐陽先生全幅真情呈露﹐你將如何交代? 但我只有遠視江水﹐默然無語。此事距今已將二十年﹐每念當時情景﹐總想流淚。但再隔一年﹐我在重慶嫁妹後﹐再去看歐陽先生。先生卻全忘前事﹐執吾手於案上﹐寫東坡詞「婚嫁事希年冉冉」數字﹐慰我以後當可更安心為學矣。我於此時復深感真正有宗教精神者之胸懷中﹐實有一不可測之寬平深廣。我後來常想﹐如我身而可分﹐我願分我身之一為歐陽先生之弟子。然我身終不可分﹐而我與佛家之緣暫斷矣。
至於對於基督教徒﹐老實說我尚未遇見如歐陽先生之使我衷心感動的人。這我相信是有﹐或是緣慳未見。但我南來香港﹐在教育界文化界的人士外﹐我所接觸的人﹐仍是宗教徒最多。除了二三佛教守院﹐我常去玩外﹐到基督教的學校﹐或修道院去講演﹐亦不下六七次。而我與牟宗三先生年來寫的文章﹐亦最為各地的宗教徒所注意。他們常有文章或書信提到﹐或加以討論。台灣有一信基督教的范仲元君﹐動輒數千字的信﹐來了十幾封﹐我實在佩服其虔誠。宗教徒之認真﹐這決非世間一般學者所能及。但我亦只有慚愧﹐實無時間對他們之問題一一答復。而在這些與基督教徒接觸的事中﹐我所比較最難忘的﹐即是在魏君的信義神學院講演之一事了。
唐君毅曾多次應邀到基督教機構講學,圖為1952年講學於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九龍支會
這事之所以令我難忘﹐是因該院之請我去講演﹐事先頗經一番考慮的。據常向我接洽的周君說﹐在一年前該院的學生﹐就望我去講演了。但是院中當局不放心﹐務必希望我只講哲學﹐不要評及宗教。我說你請院中當局放心﹐我不會在你們之神學院中﹐傷害到你們的信仰的。因這亦不合儒家忠恕之道。於是我在一晚上去沙田道風山講演了。我的講演﹐莫有什麼可說的。可說的是在道風山的山上﹐看見該院鬚眉班白的老院長。我慚愧﹐已把他名字忘了。但是我卻直覺他是一虔誠的宗教徒﹐是我在香港所未見過的。我記得他說他是北歐挪威人﹐孑然一身﹐曾在中國湘西傳教﹐三十多年﹐共黨來了﹐才輾轉到此。在我講演前﹐大家唱了詩之後﹐他便起來祈禱上帝﹐幫助我講演﹐并幫助聽講者得益。在此夜間的山上之靜穆莊嚴的神學院中﹐聽了這幾句話﹐卻使我生無限的感動。我想: 什麼力量使此老牧師由歐洲北海邊的挪威﹐到中國湘西蠻夏雜處之地﹐傳教三十多年呢? 現在為什麼他要祈禱上帝幫助我? 難道他不知道我並非基督教徒? 但對最後一問﹐我馬上了解﹐這是他們之一種禮。此禮是依於在他們之教理上﹐上帝之愛是無所不及的。不管人是否信他﹐他總是願幫助人的。然而在實際上﹐這禮同時是依於他之一超越的感情。此超越的感情是願幫助我的。但是他的謙德﹐不容許他說他有力能幫助我﹐於是只有祈禱上帝幫助我了。我又想他之祈禱上帝﹐除了幫助我講得更好以外﹐恐免不掉還要祈禱他來監臨我﹐不要我講違反基督教教義的話﹐而搖動到聽眾的信心。這是我從他們於請我講演一事之經過鄭重考慮來推測的。但是我在當時﹐雖想到此﹐卻並不覺若他真祈禱上帝來監臨我﹐便是他的狹隘﹐或是對我之不敬。我這時所引為感動的﹐是想在茫茫的天地間﹐以我這樣的渺爾七尺之軀﹐以偶然的機緣﹐在此處講台上﹐作短短二小時的講演﹐而他們亦要本他們之禮節﹐而專誠的祈禱上帝來幫助我監臨我。他們之祈禱中之超越的感情﹐究竟是為的什麼呵? 這時間講室外的松風吹過﹐我知道他們所為之什麼了。這時我心中所有的只是一種難過的悱惻。我不能分別此悱惻之感﹐是對此老牧師之為人的悱惻﹐是對上帝的悱惻﹐是對我自己對人類的悱惻﹐我亦不能分辨這與我聞歐陽先生說他七十年來﹐在黃泉道上﹐獨來獨往時所生之感動﹐有什麼差別。總之我心中是有同樣一回事而已。
但是實際上各種宗教徒之彼此間﹐及他們與我們之間﹐是不同的。如要談道理﹐一直追溯上去﹐是總有不能相喻之處﹐而說不下去的地方的。則大家雖相聚於一堂﹐而同時是天淵懸隔。這當是一永遠的悲哀。但是我知道在真正虔誠的佛教徒心中﹐他會相信我最後會成佛﹐因為一切眾生皆可成佛﹔在真正虔誠的基督教徒心中﹐亦會祈禱我與他同上天堂的。而我則相信一切: 上了天堂成佛的人﹐亦還要化身為儒者﹐而出現於世。這些不同處﹐仍不是可以口舌爭的。在遙遠的地方﹐一切虔誠終當相遇。這還是人之仁心與人仁心之直接照面。此照面處﹐即天心佛心之所存也。但在現在世界最急迫的事﹐我想還是一明儒的話說得最好﹐即「莫勘三教異同﹐先辨人禽兩路」。人道不立﹐什麼都不能說了。
以下的「讀後感」,我不會仔細區分哪些是「當年」的,是主力促成我「慕名」報讀中大的原因,又哪些是「今日」的,是我更經多年信仰反思後整合出來的。我相信前後並無二致,主要不同的,是「當年」的是說不清楚的感動,而「今日」的不過是把那些感動說清楚而已。
對於唐君毅先生的「信仰內容」,作為基督徒,我不能一一接受認同,更不能佩服到底;作為牧者,我更不得不提醒大家要小心過濾,要「適可而止」。然而,從唐君毅先生的「信仰人格」透現出來的「信仰精神」卻使我萬分懾服、感動至「恨不相逢」,不能自已。
唐君毅先生最使我驚嘆佩服的,是他對他的所信所仰那份全情投入、一身擔當、同其生死、共其榮辱的信仰精神。今天,敢問我們誰還有「信仰興亡,匹夫有責」這種信仰精神呢?朝秦暮楚、三心兩意,在「信仰自由」的幌子下,我們不但不覺回事,更覺得理所當然哩!
唐君毅先生的信念中,雖有某種「萬教同源、萬教歸一」的講法,但當心,在實際上,他本人並未真正鼓吹過任何具體的「合一運動」。他之所謂「萬教同源、萬教歸一」,只能算是一種「心願」而非學說。他甚至曾「狠下心腸」,拒絕佛學大師歐陽竟無先生收他為入室弟子的邀請,始終服膺於「獨尊儒術」的個人「呼召」,終身不改。老實說,較之於今天那些幾乎沒有底線地與「全世界」搞「合一」的所謂基督徒牧師與學者,唐君毅先生對儒學的「忠貞不二」絕對是鶴立雞群,令人眼前一亮的。說個不很妥貼的比喻,就像你看見寧死不降、戰鬥至死的敵軍,你雖然不能認同他們效忠的「對象」,但對他們效忠的「精神」卻仍是大為折服,禁不住發出「畢竟是條漢子」的讚嘆。
對於自己的所信所仰,唐君毅先生更有一種「渾身是債」的偉大情操。今天,在功利主義與功能主義的荼毒底下,我們只會問:「這個信仰對於我有甚麼用(好處)?」然後據此決定自己信不信或怎麼信。唐君毅先生卻倒過來自責自問:「我對於這個信仰有甚麼用(好處)?」然後據此決定自己一生奮鬥的方向。作為基督徒,我們不能太誇大人在信仰上的「作用」,你不去做,上帝自會興起別的人去做。但唐君毅先生強調的不是「作用」而是「責任」--永遠記得自己是個信仰上的「欠債者」,欠了上帝的「情債」,也欠了世人的「福音的債」,以致不得不戰戰兢兢地奮發自守。
為了確保自己能夠在所信所仰上不懈地奮發自守,唐君毅先生那份「居安思危」的信仰精神也是令我萬分感動,低迴不已的。他指出信仰要落實到人間,求安頓之所、望社會認同、顯名聲於世,本無可厚非,也有其需要。但一旦「落地」,就不免會有「為發展而發展」、「有了軀殼就喪失靈魂」的重大危險,扼殺原本在「飄泊無依」中奮發自守的可貴的信仰心靈。我讀聖經,讀教會史,再看看今天「主流教會」那個「越富貴越墮落」的光景,就不得不一萬個認同唐君毅先生的說法,更佩服他那份「居安思危」的先知眼界。請大家環顧今天的所謂「基督教界」,你看到有這樣的先知眼界的人嗎?
揚溢在唐君毅先生的信仰情操上的,更有一份「感天動地的信仰悲情」,一份與天地同悲的博大心胸。大家看俄網,起碼會發現到我的「基要信仰」其實與「主流教會」的無甚分別,但俄網卻有一份我自信你不大可能在「主流」那裡找到的「信仰悲情」。這份悲情,部分緣於天性、部分緣於從讀歷史文學而來的感觸、部分就是來自唐君毅先生的信仰悲情給我的深深感召和觸動。環顧四周,「主流教會」講的所謂「愛心」,多是淺薄浮面的溫情主義,比「XXX院的籌款SHOW」好不了多少。悲情不是浮泛的同情心,也不是對某人某事的一時感觸,而是將一切人間苦罪收歸本心一身擔當的「悲願」,換言之,就是一種「意想救世」而又痛於「救世無力」的悲天憫人的博大情懷。唐君毅先生大大地啟發了我的信仰悲情,靠此,我再進入聖經啟示的信仰世界,發現內裡充滿著非常近似的信仰悲情。反之,在所謂「主流教會」裡,充斥著的卻多是「迪士尼式」的淺薄愛心。這是個悲哀的事實,就是某意義下引導我進入聖經深刻博大的悲情世界的,是唐君毅先生的信仰人格而不是教會或神學院!
當然,今天,我既已立身於聖經啟示的信仰世界,就不可能全數認同唐君毅先生的信仰理念,而摩西、耶利米、哈巴谷、施洗約翰、使徒約翰和保羅等等,他們的信仰人格與信仰悲情亦斷不下於唐君毅先生,我再不能也不必把唐君毅先生的「地位」抬得太高。但是,數典不能忘祖,我之有今天,唐君毅先生卓越超群的信仰人格與信仰悲情確曾起過很大的作用,至今猶令我心存感激,不敢或忘--
艱 難 未 作 東 林 客,望 斷 關 河 念 顧 公!
結語、悲情不再,立像何為?

不久前,看到中大網站有如下的一則「新聞發佈」:
中大舉行唐君毅先生銅像奠立儀式
慶祝哲學系成立六十周年暨唐君毅先生百歲冥壽
為慶祝香港中文大學(中大)哲學系今年創系六十周年,以及該系創系系主任、首位講座教授唐君毅先生的百歲冥壽,中大昨天(5月20日)舉行了唐君毅先生銅像奠立儀式,以表揚他對哲學及文化的不朽貢獻。典禮由中大校長劉遵義教授、中大哲學系榮休教授及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勞思光教授、美國密歇根大學哲學及中文榮休教授孟旦教授、唐氏家族代表王康先生、雕塑家朱達誠先生、中大哲學系校友會會長劉國強教授、中大副校長及新亞書院院長黃乃正教授、中大哲學系系主任張燦輝教授,以及法住文化書院院長霍韜晦教授主禮,近二百名中大校友及社會賢達出席,場面熱鬧。
劉遵義校長感謝校友的捐款,為唐君毅先生鑄塑銅像。他在典禮上說:「從今以後,唐先生的銅像屹立於中大校園,他矢志發揚中華文化的精神,將永遠昭示世世代代的中大人。」 ……
http://www.cuhk.edu.hk/cpr/pressrelease/090521c.htm
銅像下面的銘文,自然極盡「歌功頌德」的能事,但是對唐先生「一九七四年自中文大學講座引退」後的事蹟,卻略而不提,似有所「隱」……
卻又幾乎在同一時間,我看到以下的一篇「舊文」,文章表面是對某個「國際學術會議」的報導,卻在有意無意之間,重提了一段在上面的銘文中「隱去」了的「舊事」,惹人遐想: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是一個慘淡的日子,新亞書院董事李祖法、沈亦珍、吳俊升、劉漢棟、郭正達、錢賓四、唐君毅、徐季良、任國榮等九人發表辭職聲明,其中「聯合制終於被棄,改為單一集權制……同人等過去慘淡經營新亞書院以及參加創設與發展中文大學所抱之教育理想無法實現……是非功罪,並以訴諸香港之社會良知與將來之歷史評判」,一字一句,滿是悲情。
二十八年後的今天,悲情不再。……
http://www.inmediahk.net/node/20141
為了「查明真相」,我最近就買了一本《唐君毅傳略》來看,末後有一篇由另一位大學者徐復觀先生寫的悼辭,閱後更使我感觸良久:
將上述三篇文章一併觀之,我只能感喟:「日光之下無新事!」人在之時,不見得「廣受歡迎」,甚至終於鬧得「不歡而散」。現在人走了(更好是死了),不再「成為威脅」了,就拿來做「招牌」,給他建碑立像了。然而,「悲情不再,立像何為」?
當然,沒有基督的「基督教」、沒有共產理想的「共產黨」,今天滿街都是,這樣,多一個沒有悲情的「唐君毅(像)」,倒又有何話可說?
葉公好龍,古今一例,否則,救世主又如何會死在十字架上?
唐先生一生忠厚,卻錯在太忠厚,對人太樂觀了。他認為基督教(當然是指原裝正版的基督教)把人看得太悲觀,太強調人的無能了,但觀乎唐先生的境遇,我怕基督教還是對的!但我不忍深責唐先生,特別當我看到今天「人大過天」的所謂「基督教」,我疑心唐先生的「儒教」可能更近於原來基督教。
網頁上載後,再到九龍桂林街新亞書院的舊址一看(鄰近黃金商場),又拍下了一些照片。




原址及附近的樓房已列為「市區重建項目」。我生得太晚,自然不是「新亞校友」,讀中大時原先是報了新亞書院,但後來卻被分派到崇基書院,所以對新亞本身,我說不上有很重的感情,有的,都是連繫到對唐君毅先生的崇敬上面的,頗有一點間接。但見此情此景,想到重建「建築」容易,重建「生命」與「信仰」卻難,唐君毅先生的一生就是最好的寫照,禁不住又是一陣唏噓……